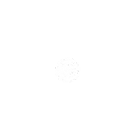发布时间:2022-05-15
2022年5月13日上午,山西大学120周年校庆“科技史系列讲座”第八讲开讲,我所邀请到了广西民族大学科技史与科技文化研究院容志毅教授以“腾讯会议”的形式作了题为《蛊毒实证研究:兼论“四重证据法”》的学术报告。此次会议由我所王坚副教授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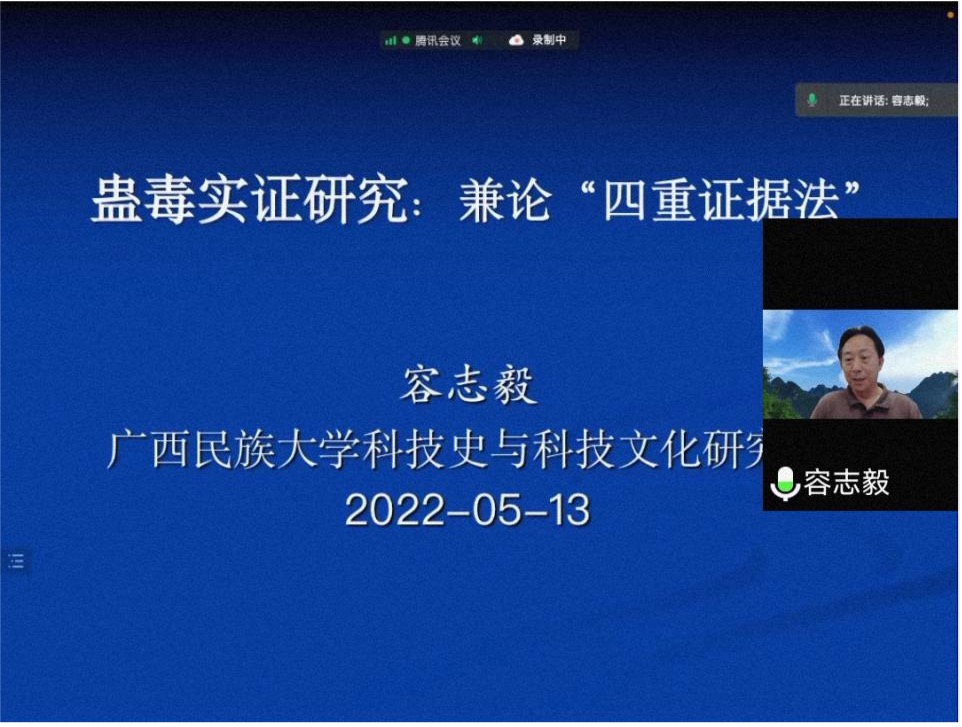
讲座伊始,主持人就容志毅教授的个人经历、研究方向、学术成果以及报告主题等进行了介绍。
容教授以2009年7月在“第16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大会”所作关于蛊毒研究的报告为切入点,提出了“巫蛊:强势民族和强势文化对弱势民族和弱势文化的栽赃?”的问题,继而对蛊毒的本质以及四重证据法在蛊毒研究中的应用与实践问题展开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一、从历史看巫蛊
历史上,在殷商甲骨文中已有关于蛊的文字记载。甲骨文的“蛊”字外面是一个器皿,里面是两条虫,也有些甲骨文画了一条虫或三条虫。甲骨文是一种象形文字,可见殷商时期是先有制蛊之事,而后再按照这个事件的外形去模拟、创造“蛊”字。
从汉代到魏晋时期的律法中也有对蓄蛊者严加惩罚的记载。当时的法律对放蛊行为的惩罚非常严重,凡是被人状告蓄蛊或放蛊的,一经发现严惩不贷。据《北史》记载,南北朝时因放蛊人数众多,中央政府不再将蓄蛊、放蛊者砍头,而是将其投放至四夷。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被投放到南方楚越之地的蓄蛊、放蛊者在南方多雨潮湿、蛇虫出没频繁的气候与地理环境下,行蛊之事如鱼得水。蛊毒虽然在中原地区产生,但其发展重心却是在中国南部地区,另有其历史原因。
二、20世纪30年代巫蛊进入学术视野
中国学术界对蛊毒的系统性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北方高校南迁之后,学者们在和南方当地民族相互交往过程中,发现很多南部的民族在茶余饭后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谈起巫蛊。关于巫蛊的传闻逐渐引起了南迁高校学者的关注。其中,较早对蛊毒予以关注的是凌纯声和芮逸夫两位民族学家,凌、芮二人借鉴国外民族学田野理论与调查方法对湘西苗族地区进行考察。在其撰写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讨论较多的是湘西的蛊毒(巫蛊)。改革开放后,邓启耀、陆群、黄世杰等人对云南、湘西、广西等地的巫蛊进行了考察。据统计,相关蛊毒研究的论文约有七八十篇,但均未能够说明蛊毒究竟为何物。
隋唐时期,孔颖达在其论著中曾对蛊毒定义:“以毒药毒人,令人不自知者,今律谓之蛊毒。”这是在史料文献中对蛊毒的最早记载。“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将制蛊描述为:“取百虫入瓮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食诸虫,即此名为蛊。”其与民间流传五月初五入山捉百虫入瓮,令其相互残食,所剩之虫即为某某蛊虫毒的说法一脉相承。
三、童年的巫蛊记忆与学术之思
容教授介绍到,自己之所以对蛊毒研究产生兴趣,离不开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早在孩童时期便已对海南黎族的放蛊耳濡目染。结合自身的经历,容老师分别阐述了海南黎族制蛊、放蛊的过程。
与非洲巫毒教在野外将动植物、矿物等30多种原料混在一起并用锅头熬制巫蛊的工艺和方法颇为不同的是,中国的蛊毒是在一种正常的环境里面滋生出来的霉菌。巫毒教所制毒药毒性非常强,在非洲巫毒教的教区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像僵尸一样不停劳作的年轻人,他们被放毒之后处于一种假死的状态,没有呼吸,没有脉搏,也听不到心跳。这时非洲当地人就会把中毒假死之人埋葬。在一定时辰之内,巫毒教又会趁黑把这些假死之人挖出来,给他们吃上解药。第一个被唤醒之人将成为后续被唤醒者的指挥官,他们的一举一动均来自指挥官发出的指令。
在中国的苗区、黎区,只要知晓放蛊之人,人们都会有意地疏远。“倮胞议婚,若访明某家为药王,则不与通婚。”这是马学良先生在《倮族的招魂与放鬼》中对云南彝族地区放蛊现象的调查。但容教授在贵州苗族地区的考察结果与马先生的田野考察结果不同,容教授发现贵州苗族的蛊女(蛊妇所生之女)也能如常人一样可以结婚生子。蛊妇所生男孩,其婚姻基本不受影响。但由于当地制蛊秘术传女不传男,蛊妇家的女孩出嫁比普通人家的闺女要难。过去,在贵州苗族地区蛊妇家的女儿能够通婚,一般会采取骗婚、放蛊人家互相通婚或因感情深厚坚持嫁娶的三种方式。
四、文献与田野互证
现存文献史料对蛊毒的确切记载尚不多见。晋人李石在《续博物志》中有载:“胡蔓草(断肠草)出二广......或取毒蛇杀之覆以此草,浇水生菌為毒药害人。”此外,宋代方勺的《泊宅编》:“先用毒蛇,不计多少杀埋庭中,浇以米泔,令生菌,因取合药。”李氏与方氏所载制蛊方法略有不同。胡曼草出自广东、广西。制蛊者把毒蛇打死之后,用断肠草盖在蛇的身上,再浇上水,令毒蛇处在一种黑暗潮湿的环境之中,这与海南黎族制作蛊毒的方法颇为相似。从甲骨文的“蛊”字来看,黎族原始的制蛊方法可能更接近其字意。相较于田野考察所发现的海南黎族的传统制蛊方法,容教授认为《续博物志》《泊宅编》的记载未能真实再现蛊毒制取的原样。事实上,这些史料来源并非制蛊的真实场景,而是道听途说,这也就是蛊难以捉摸的原因之一。前辈学者受宗教的,习俗的因素限制,在实际的田野考察中很难目睹蛊*的制作工艺。

五、蛊毒的实证研究
蛊毒流传几千年,作为一种黑巫术,单靠历史文献与田野的互证难窥其真容。为此,容教授选择对蛊毒进行科学的实证研究。历经多次试验,在汲取黎族、苗族所流传的制蛊经验的基础之上,容教授先后在广西民族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实验室借助先进的科学仪器设备对蛊毒进行检测、化验、分析,并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其研究成果被拍成纪录片收录在中央电视台CCTV9纪录片栏目。

六、关于“四重证据法”
不论是黎族、苗族地区所流传的蛊毒传闻,还是非洲巫毒教所熬制的毒药以及容教授所研制的霉菌。蛊毒确有其物,并非是一种虚幻,其能够在千年的漫长岁月得以流传,自有其物质基础。通过对巫蛊的考察,容教授深感若仅从文献或考古的角度,很难分析蛊毒背后的因素。如果在方法论层面不继续进行拓展,研究就会受到限制。针对现有“三重证据法”,容教授作出了解释。一重证据法(即传统考据学,从文献到文献的一重证据法),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的一种治学方法,如乾嘉学派。二重证据法,王国维于1925年首倡,是取“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这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尤其是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三重证据法,学界比较认可的三重证据法是民族学家黄现璠所提倡的将文献、考古发现、田野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叶舒宪先生在上述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将口碑材料称为“第三重证据”,将文物和图像称为“第四重证据”。容教授认为叶教授的“四重证据法”实际上是将三重证据拆分成了四重。
基于此,容教授提倡在三重证据法的基础之上再增加一重实证的研究方法。即以古籍文献、考古发现、田野材料和实证研究四重互证的方法研究人文学科。
报告接近尾声,容教授指出,在民族学、人类学乃至更宽泛的人文学科的研究中,由于一些历史的、宗教的、信仰的和习俗的原因,问题难以通过文献、考古、田野的方法得到解决。因此,需借助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文献、田野及民族志资料进行模拟、复原、测量及分析,以获得对问题的较为真实的诠释。因此,“四重证据法”的提出应成为人文学科积极倡导与践行的方法。
最后的互动提问环节引发了师生的热烈探讨,姜守诚教授、杨小明教授、仪德刚教授、史宏蕾教授以及部分校内外的听众先后就史籍文献中的放蛊与解蛊,箭毒物及其药性,“口述史”研究方法在现行的“四重证据法”或“五重证据法”研究方法中的归类,蛊毒的心理精神暗示作用,蛊毒秘术的传承及其社会影响,蛊毒与符咒等问题与容志毅教授展开了积极的讨论,与会师生受益良多。
通讯撰稿 | 任世君
通讯审稿 | 袁紫玉
网页编辑 | 王 坚